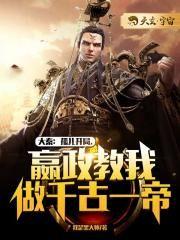精英小说>去父留子后才知,前夫爱的人竟是我 > 第371章 三只小团子(第1页)
第371章 三只小团子(第1页)
“是哦。”溟西迟装傻的点了点头。
“所以……”
“所以袁家主为什么又吃又拿呢?你是想等南荣琛一走,吞并南荣家,一家独大。袁家主,这样的算计,我溟家站在一旁看着,也想分一杯羹呢。”
袁松屹放在膝盖上的手紧了紧,“你到底想要什么?”
“我想要什么,在于这段录音在袁家主心里的重要性。”
袁松屹没说话,看着眼前城府深沉的男人,道:“从前只觉得溟野本事了得,可论起算计来,他还是要输给你的,你想让我帮你拿到溟家。。。。。。
海潮在暮色里低吟,像一首永不完结的安眠曲。夏南枝坐在礁石上久久未动,耳边的钢琴声早已随风散去,可那旋律却如根须般扎进心底,一圈圈蔓延。她闭上眼,任咸湿的风吹乱发丝,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前那个雨夜??程砚舟站在医院走廊尽头,手里攥着一份胎儿脑波图,眼神亮得惊人,像是握住了宇宙唯一的密钥。
那时她还不懂,他眼中燃烧的不是科学的狂热,而是绝望中生出的执念:一个听不见世界的孩子,能否听见爱?
如今答案已铺展成海。
手机还贴在胸口,那段音频循环播放到了第三遍。没有高潮,没有炫技,只有极简的几个音符来回流转,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着敲击墙壁,试图确认另一侧是否有人回应。这不再是《潮汐信笺》的任何一版乐谱,而是一封纯粹用心跳写就的独白。夏南枝忽然明白,这第一百零一封信,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寄给她。它是写给时间的,写给等待的,写给那个曾在手术台前发誓“宁可毁掉自己也不伤害她”的男人自己的救赎。
她轻轻将手机收进衣袋,起身时看见念念正朝这边跑来,裙角沾着细沙,脸上漾着笑意。
“妈妈!”女孩的声音清亮如铃,“小宇刚刚用手语说,他梦见爸爸弹琴了!”
夏南枝心头一颤。小宇是基金会新收的孩子,先天全聋,三个月前才第一次接触“潮汐协议”的基础训练。按理说,他对程砚舟毫无认知。
“他说梦里的钢琴浮在海上,你和爸爸都在上面。”念念比划着补充,“而且……曲子是你日记里写的那首未完成的变奏。”
夏南枝怔住。那首曲子,是她在离婚后某个深夜独自写下的,从未示人,甚至连林清漪都不知道存在。它没有正式命名,只潦草地标注为《如果那天我没转身》。后来她把它撕了,碎纸片撒进了海。
可现在,一个素不相识的七岁男孩,在梦中听见了它。
她蹲下身,捧住念念的脸:“你是怎么知道这首曲子的?”
念念歪头想了想:“我不知道啊,但刚才教手语的时候,突然脑子里就有了这段旋律。就像……有人轻轻哼给我听。”
夏南枝脊背泛起一阵微麻。
这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。自从岩洞三重奏之后,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两百例“自发性旋律记忆”报告,患者多为听障或自闭症儿童,他们能准确复现《潮汐信笺》不同版本中的冷门段落,甚至补全残缺音符。最离奇的一例来自西伯利亚村庄,一名老年痴呆症患者在生命最后三天突然清醒,完整演奏了一段从未学过的钢琴曲,并坚称“这是那个海边父亲留给所有孩子的礼物”。
林清漪称之为“群体共感溢出效应”,认为87。3赫兹的共振已突破个体神经系统的边界,开始在人类集体潜意识中建立临时通路。换句话说,程砚舟当年试图编码的“情感传递系统”,正在以一种无法预测却无比温柔的方式自我演化。
而念念,似乎是这个网络中最敏感的节点。
当晚,夏南枝翻出尘封已久的旧硬盘,试图找回那首被撕毁的曲谱。数据恢复软件扫描良久,最终只拼凑出零碎片段。她正欲放弃时,终端忽然自动跳出一段MIDI文件,标题正是她亲手写下的那句??《如果那天我没转身》。
可问题是,她从未上传过这份文件。
更诡异的是,播放时,背景里竟隐约叠着另一个声部:稚嫩的手指在琴键上试探性地按下几个音,节奏缓慢,带着孩童特有的犹豫与认真。夏南枝猛地意识到??那是念念三岁时的录音样本,曾用于早期神经反馈训练,早就该被系统清除。
她颤抖着放大波形图,发现两个声部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相位差,恰好构成八度和鸣。也就是说,现在的她与过去的女儿,正在通过某种未知机制隔空合奏。
眼泪无声滑落。
这一刻她终于看清,程砚舟当年真正想做的,从来不是制造“完美倾听者”,而是搭建一座桥??让那些因生理、心理或命运阻隔而无法对话的人,能在音乐的维度里重逢。哪怕一方已失聪,一方已遗忘,一方尚未来到世间。
只是当时,他们都太痛了,痛到看不见这份心意背后的光。
第二天清晨,念念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奔向钢琴。她说昨晚做了个奇怪的梦,梦见海底有一座发光的城市,街道由音符铺成,居民都用手语交谈,而城市中央矗立着一架巨大的透明钢琴,里面坐着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,正对她微笑。
“我知道他是爸爸。”她轻声说,“虽然我没见过他年轻时候的样子,但我认得他的手指动作??和视频里一模一样。”
夏南枝没有质疑。她只是默默打开通讯器,拨通了林清漪的号码。
“我要重启‘摇篮计划’档案库。”她说,“不是为了研究,是为了归还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