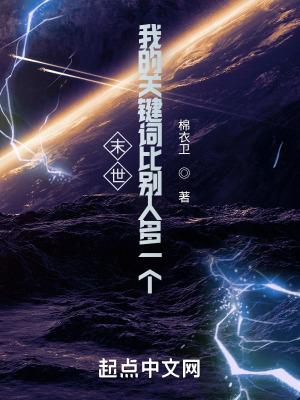精英小说>当过明星吗,你就写文娱? > 第二百一十二章 世纪大和解(第2页)
第二百一十二章 世纪大和解(第2页)
当晚,他在镇上唯一的旅馆住下,连夜整理录音。当他把听诊器连接到高敏麦克风,再接入降噪系统时,墙体中的声音愈发清晰。他甚至分辨出一段对话??一对夫妻在争论要不要堕胎,女人哭着说:“可这孩子是在饥荒年头怀上的,他是活下来的证明啊……”那是1961年的事。
他把这些声音剪辑成一部十分钟的音频作品,命名为《墙的记忆》。发布时,他附了一句话:“我们总以为历史写在书上,其实它最先发生在耳边。”
三天后,这条音频登上热搜。无数人留言说自己童年老屋的墙壁也有类似感觉;一位建筑师发起“倾听老建筑”行动,组织团队为全国百年民居做声学扫描;更有学者提出“声景考古”概念,主张通过环境残留音重建社会记忆。
而长岭镇,也开始热闹起来。有人专程前来“听墙”,带着耳机贴在土坯上流泪;有学生来做田野调查,记录老人口述史;甚至有音乐人以此为灵感创作交响乐。
周志民却始终坐在院子里吹笛子。他对来看他的记者说:“我不是什么声音先知,我只是不愿意看着人们把苦咽下去。”
一个月后,余惟接到文化部通知,《人间和声》项目正式被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,成为首个以“声音叙事”为核心的文化工程。同时,教育部决定在全国中小学增设“倾听课”,每周一节,内容不限于音乐,而是训练学生聆听他人、理解沉默、识别情绪背后的声音信号。
但他没留在北京领奖。他去了西北戈壁,那里有一座废弃的气象站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三位气象员在此驻守三年,每日记录风速、温度、云层变化,却因通讯中断与外界失联整整十个月。其中一人在日记里写道:“我们还在报数,但我们不确定还有没有人听。”
余惟找到当年唯一幸存的老兵李振国,如今住在兰州郊区。老人颤巍巍地拿出一盒磁带:“这是最后一盘录音,没来得及发出去。你要是感兴趣,就拿去吧。”
磁带上写着:“1983。11。07最后一次例行播报”。
余惟回到工作室,戴上耳机播放。起初是标准的气象数据播报,语气冷静专业。到了中途,背景风声骤然增强,播报开始颤抖。突然,一个声音哽咽着说:“同志们,我不知道这段能不能传出去……但我们一直都在岗。今天是我女儿生日,她五岁了。我想告诉她,爸爸没逃,爸爸一直在看天。”
另一人接过话筒:“我也说一句。老婆,对不起,我没能在娘临终前赶回去。但我每天都在替她望着这片天空,干干净净的,像她的心。”
第三个人沉默很久,最后只说了三个字:“我还活着。”
余惟听完整盘录音,整整一个小时没有动弹。第二天,他联系国家气象局,提议设立“沉默观测日”??每年11月7日,全国气象站同步关闭自动传输系统,改由人工播报一次完整数据,并公开历史上所有未送达的记录。
那天,当全国各地上百个站点同时响起人工播报声时,许多老气象员热泪盈眶。一位退休站长说:“我们不怕孤独,怕的是付出不被知晓。”
与此同时,《超级新声》节目组主动联系余惟,邀请他担任新季评委。这一次,他们修改了赛制:初选不再看外形、舞台表现或话题热度,而是要求选手提交一段“原生声音档案”??可以是家乡的鸡鸣狗吠,母亲做饭时锅铲碰撞声,父亲修车时的咳嗽,或是自己第一次哭泣的录音。
首期节目中,那个曾被淘汰的农村女孩再次登台。她播放了一段音频:凌晨三点,她家大棚里的卷帘机启动声,夹杂着父母踩着泥泞走动的脚步,还有她一边摘菜一边背英语单词的轻声朗读。她说:“这就是我的音乐。它不华丽,但它真实。”
全场静默。评委之一,曾质疑她的顶流歌手站起来鞠躬:“对不起,我之前不懂什么是声音的力量。”
节目播出后,“原生声音计划”迅速蔓延至影视、文学、广告等多个领域。品牌不再雇佣专业配音员念广告词,而是采集用户真实语音;小说出版时附赠作者写作时的环境音CD;甚至连法院庭审都开始引入“情感语调分析”,辅助判断证词真实性。
余惟依旧在路上。
秋天,他走进大兴安岭深处的鄂温克族猎民点。一位年迈的萨满递给他一根鹿骨哨:“这是我们祖先召唤驯鹿的工具。现在鹿群少了,声音也快断了。”余惟将哨音录下,结合森林里的溪流、松涛、雪落之声,创作出《林语密码》,并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上播放。一位科学家听后落泪:“原来生态保护,不只是保物种,还要保它们的声音生态。”
冬天,他来到深圳某科技园区,探访一群AI训练师。这些人每天要听数千条语音样本,标注情绪、语气、地域特征,以便让智能助手更“人性化”。但他们自己却长期处于高压中,许多人患上听觉疲劳症,甚至失去对真实情感的感知力。
余惟为他们举办了一场“反向聆听”工作坊。他让每个人闭眼,播放一段自己童年最爱的声音??有人是外婆摇扇的??,有人是小学放学铃声,有人是初恋递情书时手心出汗的黏腻感。然后他说:“你们教会机器听懂人类,但别忘了,你们也是人类。”
活动结束后,一家头部公司宣布调整算法伦理准则,新增一条:“任何语音模型不得模仿真实个体声音,除非获得其知情授权。”并设立“声音人格权基金”,用于补偿被滥用音源的普通人。
2027年春,余惟受邀在哈佛大学演讲。主持人介绍他时用了很长一段话,最后问:“您改变了这么多人的生活,有没有一刻想过停下来?”
他摇头:“不能停。因为只要还有一个地方有人不敢说话,还有一段声音未被听见,我就必须继续走下去。”
台下掌声雷动。一名学生举手提问:“如果有一天,所有声音都被记录了,我们会不会反而失去了倾听的能力?”
余惟沉默片刻,答道:“技术能保存声音,但只有人心才能赋予它意义。就像你现在问我问题,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,而是你愿意问。”
回国后,他收到一封信,来自青海湖观鸟站那位志愿者。信中说,今年斑头雁迁徙途中,G-17的后代成功抵达越冬地,追踪器显示它的飞行轨迹恰好画出一个音符形状。
“我们给它起了名字,”她写道,“叫‘回声’。”
余惟站在阳台上,望着夜空,手中握着那枚排爆战士送的弹壳。远处城市灯火通明,车流如河,人声鼎沸。他知道,在这亿万喧嚣之中,仍有无数微弱的声音正在等待被听见??病房里的最后一句呢喃,流浪猫躲雨时爪子刮地的轻响,失业者撕碎简历时纸张断裂的脆音,独居老人按下电视开关的孤寂按键声……
他打开笔记本,写下新的一章标题:
**《下一秒,是你》**
风穿过窗棂,带来远方铁轨的震动。他知道,旅程仍在继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