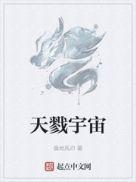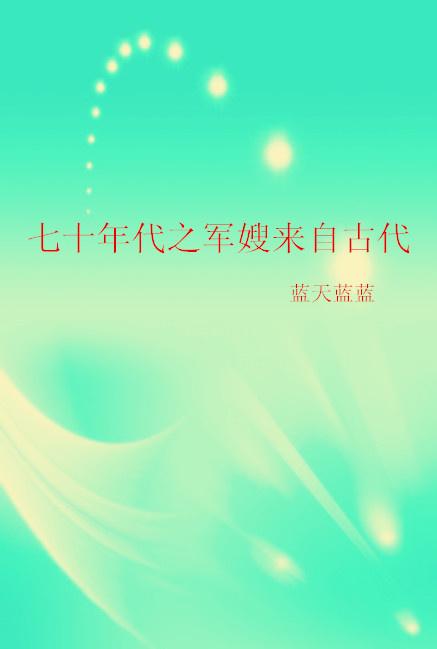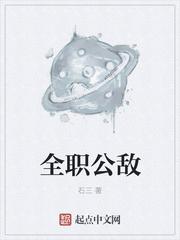精英小说>大清疆臣。 > 第五十四章 少女之思(第2页)
第五十四章 少女之思(第2页)
她自然不知道,在孔庆镕眼中,自己的脸上,阵阵红晕已然压过了白嫩的肌肤,便似一只水蜜桃一般颜色。
孔庆镕看姐姐面色,自然也忍俊不禁,道:“姐姐不要掩饰啦,姐姐,你自己找片镜子来看看罢,你是不会说谎的。不如姐姐先告诉我,姐姐看上的是四氏学里哪一位兄长?只要姐姐告诉我,我不会告诉爹爹的。”
“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讨厌?!你再乱说一句,看姐姐不打你!”
“姐姐且住!男女授受不亲,姐姐都十八岁了,应该自重才对。”
眼看最为惯用的威慑之术无效,孔璐华只好又坐了下来,忽然,她双目之间,竟是异常莹润,竟似要掉下泪一般,道:“弟弟,你这般欺负姐姐,你忍心么?你忘了去年的时候啦?当时伯父刚去世,爹爹让你过继给伯父,你那时是何等孝顺,在伯父灵前,足足哭了两天两夜。那几日正值初冬,夜里寒冷,你又要按旧礼赤足守灵,一个晚上过去,脚都冻裂了。你忘啦?当时还是姐姐给你找了药敷上,姐姐还用帕子给你裹了伤呢。当时姐姐还想着,姐姐的帕子质地好,给你裹了,也教你暖和些,又不废礼数。姐姐对你这般好,可现在你……你竟这样奚落姐姐……你说,你还有良心吗?”说着说着,玉颊之上,竟也渐渐出现了两道细细的泪痕。
孔庆镕听着这番言语,却也隐隐想到,姐姐这一番话,自己其实完全无从辩驳。他入继大宗,视伯父至孝,几甚于生父,孔璐华是自己姐姐,也自当依礼尊重,若是这句话上还要反唇相讥,只恐自己在孝悌一事上,声名将大大有损。又看着姐姐一个白梅一般的美人被自己气得泫然欲泣,心中也不是滋味,便冲口而出,道:“姐姐,是弟弟错了,姐姐去四氏学的事,弟弟不该管的。姐姐有心上人,便藏在心里就好,也不用告诉……”
“姐姐没有心上人!”
忽然门外一个声音道:“璐华,这又是怎么了?刚才庆镕来问你外出之事,怎么过了这许久,还不见动静?”这声音二人自然熟悉,说着,一个儒雅的中年人走进书房,自然是孔庆镕之父孔宪增了。
孔璐华连忙给父亲行过礼,孔庆镕也拿着那幅字,跑到父亲面前,道:“爹爹,姐姐做了好多诗,我正问姐姐呢。你看,姐姐好厉害,连英吉利是什么却都清楚呢。”他虽已入继大宗,但此时院中只有三人,便依着旧习,继续称孔宪增为爹爹。
孔宪增也不知道英吉利是什么,但毕竟自己是二人之父,便道:“庆镕啊,璐华读书多,经史诗文都有涉猎,便是四氏学里那些男子,见识也未必及得上璐华呢,你却要好好向你姐姐学习才是。不过……”回头一看,那两幅新字犹为显眼,孔宪增也不禁沉吟,道:“这两首诗却不像璐华所作,只是语出何人,爹爹也不清楚。”
孔庆镕也跟着问道:“爹爹,你看那首诗,写着淡红残雨的,最前面却还有两个字,笔画好多,却是什么?”
孔宪增看了一眼,道:“这两个字啊,念作‘瀛台’,这个地方爹爹之前去过的,就在京城里面,距离咱京城里的衍圣公府,也只有里许。爹爹当日和兄长一起入朝面圣,皇上特赐我二人赴瀛台一游,风景确是甚佳。可是璐华,你也没有出过曲阜,却怎的知道瀛台的模样?”
孔璐华眼看父亲前来,想再像对付弟弟那般以情服人,却是用不得了,只好回道:“回……回爹爹,这瀛台女儿确实没去过,是……是前些日子,四氏学里一位曾家哥哥从京城回来,说他路过瀛台,看了一眼外面风景,女儿听他说瀛台风景如画,才……才这般写了玩的……”
孔宪增看女儿神色,已猜得三四分,却也不甚在意,又问道:“那这一首却又如何,璐华,你自己且看看,这‘华年’、‘明珠有泪’、‘惘然’之语,却和李义山那首《锦瑟》,用得是一模一样的韵脚,而且其中典故,也直接引用了数处。你以前学诗的时候,爹爹可听你说过,似这般旧典频出之作,定是出自庸夫俗子之手,你便看一眼也是多余。怎么,今日竟然做起这般诗句来了?”
孔璐华只好回道:“爹爹,这……这诗是女儿前些日子,路过四氏学的时候,听得里面几个童生抱怨,说去年题目太难,自己答不上了,又要耽搁一年。女儿看那几个童生,年纪却也不小了,想着竟还未能成学,实在可怜,才有此作。当时……当时只觉得字写得还算好看,就装裱了起来,却……却没想过别的。”
孔宪增仔细看着轴上诗句,却暗自露出了笑容,道:“想来璐华这几个月里,诗才大进,定是四氏学中,又出了什么不世出的奇才。不如这样,孩子,若真是四氏学里的,你中意哪一个,便只管和爹爹说,爹爹去帮你问问,看他是否有求亲之意,如何?”
孔璐华脸上自然又是一阵羞红,道:“爹爹您怎么……怎么也取笑其女儿了,四氏学……就四氏学里那些个不肖子弟,我才瞧不上呢。爹爹,今日不是说要去看沂水吗?轿子可也备齐了?若是已经备好,我们便过去吧,沂水的风景,也有好久没看了呢。”
孔宪增仍然是一副满不在意的样子,只带了孔庆镕先出了门,孔璐华也随即掩上了书房门户,看着父亲和弟弟的背影,终于暗自松了一口气。
那个人,可不是想猜就猜得到的……
到了五月,阮元的督学工作还要继续下去,下一站是泰安,而出发之前,之前各府的遗卷搜录也在继续进行。这一日杨吉将车马收拾已毕,便到学署来找阮元。
入得学署正厅,只见数百份卷子散落在一边,阮元和焦循手中各执一卷,却一直在沉思着什么,迟迟没有动静。杨吉见了,也自然心生烦闷,决定找些乐事,便道:“伯元,这次出发,是要去泰安府么?我听说去泰安那边,肯定要路过泰山,是个了不得的地方呢。伯元,你要不要也去看看?”
“那便去吧,我也正想着去看看呢。”没想到出游的事,这一次阮元答应的如此爽快。
杨吉也是一愣,不知阮元为何转了性了。焦循眼看他神色,便替他问出了这个问题:“伯元,你在山东这半年的事,我可都听说了,那可叫一个大公无私啊。每到一处,不是主持考试,就是收集金石遗物,连特产都不买些回来。这一次他说要去泰山,你竟然答应得这般爽快?想来这泰山之名,总是天下皆知,这才让你这不食人间烟火之人,也动了凡心啊。”
“你们啊,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”阮元却依然心平气和,道:“这泰山之上,有一座碧霞元君之庙,之前家中一直供奉,这一次来了,自然要去参拜一番。另外,泰山刻石颇多,这次过去,也要多加搜录,以便记述山东金石之事,不是吗?”
“这人平时都在想什么……”杨吉听了,也不禁疑惑。
阮元又忽然问道:“里堂,之前托你去问问武先生,眼下怎样,可是与他有联络了?”
焦循道:“伯元,这武先生啊,人倒是不错,我看他家就那么大地方,还收集了不少金石遗物,书法字画呢。平日和他说起学问,这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也自然多讲了一些。看他神色,和我应该聊得来,当然了,你找他入幕的事,我还没说。”
“这次我去泰安,你便问问他有无入幕之意吧。这些日子,金石古物收集了不少,看起来也确实需要一位大家指教才是。”阮元道。
杨吉却看着阮元手中的卷子,问道:“伯元,你这卷子我从进门起,就看你一直拿在手里,怎么,他写得很好么?要是写得好,你把他录取了不也就成了?却为何还要拿着不放呢?”
“你有所不知。”焦循道:“伯元手里这篇卷子,是一个叫郎炳的童生写的。伯元出的题目是论方田水利兴建。这个叫郎炳的年轻人把算学里的勾股之法,用在了田亩清丈之上,我和伯元都通一些算学,故而知道其所言皆有道理,并非空谈。只是……这郎炳的四书文卷子我们也找到了,两篇四书文做得平平,只能说没有不合规制之处,是以伯元才会犯难,不知是否要补录他。”
“还有里堂手里那篇卷子。”阮元道:“我出的题目是白桃花,里堂那篇诗是个十三岁的童生所写,其中有两句‘惆怅武林溪上客,清风皓月再来时’。这般气度意象,倒是童生中少有。名字……是叫陈官俊吧?若论诗文,拔擢他成学也在情理之中,只是这番年纪……却还需要再思量一番。”
“伯元,你不是平日也总说,那什么八股文,作了也没用,要选的是真才实学之人吗?怎么?我听焦相公这般言语,这郎炳是个真才实学之人,你却又不敢取录他了?”杨吉道。
“杨吉,这番道理,天下学政十有八九都懂。你这般说,也不会有人反对你,可真的坐到这个位置,要考虑的就多了。”阮元道:“若今日选了他,却将一个八股做得不错的童生黜落下去。日后童生之中,必定会有怨言,说我取士全凭所好,却不顾规矩。想来天下学政,十有八九不喜八股,却又不得不用八股,也是这般道理吧?”
“这陈官俊的事却也一样。”焦循道:“前明张江陵的事,你或许不知,可却是约定俗成,童生年纪过小的,往往抑而不录。说是为了让他们学业更成熟些,其实也是照顾那些年长的童生。若不是这种道理,想来伯元当年十五岁去应县试,刘大人就算严于规矩,总也能将伯元补录进去,那不过是县试,而我们眼下要选的,可是生员啊。”
“什么约定俗成,什么不得不用?”杨吉听二人这般解释,却不免有些着恼,怒道:“伯元,你平日和我说起这八股文,从来都是一句话,这八股没什么用,选不出真才实学之人。你说做什么官,便该做什么事,这我也由着你,你做了这山东学政,难道不该选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出来么?你说清丈田亩,我听着是个好事啊,若是这个叫郎炳的,日后把他所学用在田间地头,还不知会帮助多少百姓呢!这样的人你不去选,却要选那些没用的废物?还有,年纪大怎么了,年纪大就不会坑害百姓了?我看有些人年纪越大,心还越黑呢!伯元,你忘啦?咱当年考进士的时候,是怎么想的?眼下你这般言语,却和那些一无是处的官老爷还有什么区别?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