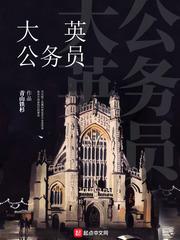精英小说>穿成带娃和离妇,盖房囤粮当首富 > 第二百一十章 见世面(第1页)
第二百一十章 见世面(第1页)
她派去打探的人,依旧什么都查不到。
苏玉娘的日子过得简单规律,要么在铺子,要么在家,要么上山,接触的人也都是些寻常百姓或生意伙伴,根本没有什么可疑的“幕后高人”。
沈观和灵悦那边更是滴水不漏,除了医馆和偶尔去苏家,几乎不出门,也查不到任何有用的背景信息。
她试图抬高香料价格,苏玉娘那边却总能“恰好”找到替代品,或者干脆推出了不需要那种香料的新口味卤味,影响微乎其微。
她试图收买村民,可如今苏家在村里的声望如日中天,那些与苏家合作的村民都死心塌地,根本没人愿意为了她那点小恩小惠去得罪苏家。
至于那些谣言,更是如同石沉大海。
苏记的吃食干净美味,价格公道,老主顾们根本不信那些鬼话,新顾客尝过之后更是成了回头客。
县衙那边因为周县令和林大人的看重,对苏家更是多有照拂,一些针对铺子的捕风捉影的小报告,都被李师爷压了下来,甚至还派衙役加强了麻食街和卤味铺周边的巡逻。
而苏老汉那边,更是让她无处下手。
那老头子虽然看着老实巴交,但在种地育苗这件事上却是一丝不苟,再加上有苏玉娘在旁边时时提点,根本抓不到任何错处。
反而因为他尽心尽力地指导村民育种,改良农具,在县衙和村民中的声望越来越高。
苏家的生意,就像那烧旺了的灶火,不仅没有被她的暗箭扑灭,反而越烧越旺!
卤味铺成了县城里的新招牌,日进斗金;狼牙土豆摊依旧火爆;新推出的酸辣粉、调料包也备受追捧;连带着整个苏家村,都因为豆芽种植和给苏家做工,在旱年里焕发出了别样的生机!
她的挫败感与日俱增。
随之而来的,是更深的恐慌感。
苏家仁没有夭折,反而考上了县里最好的书院!
她开始怀疑自己,怀疑那些支撑她走到今天的记忆。如果连苏玉娘的命运都能改变,那袁川呢?他还会像前世一样官拜宰相吗?她的谋划,她的未来,还能实现吗?
几日后,苏玉娘将铺子和家里的事务仔细安排妥当,卤味铺交给苏家平全权打理,苏二林和沈氏协助,狼牙土豆摊交给苏老太和卢氏,苏一木苏三森负责田地和作坊建设。
苏玉娘便带着苏老汉和苏家仁,与提前返回县城做好准备的周县令等人,踏上了前往京城的路途。
考虑到苏老汉毕竟受过伤,年纪也大了,加上苏玉娘如今是朝廷亲封的“安康乡君”,身份不同以往,周县令在安排行程时格外用心。
他特意调拨了两辆内部铺陈着厚实软垫、车厢宽敞稳当的官用青篷马车,一辆供苏家三人乘坐,另一辆他与李师爷、李主事共乘。
此外,还专门配备了十余名骑着高头大马、身手矫健的精干衙役随行护送,一路上的食宿也明确由官府承担,沿途驿站皆需好生接待,这待遇,对于第一次出远门的苏家人来说,不可谓不周到。
苏家仁坐在柔软舒适、几乎没有颠簸感的马车里,感觉像是做梦一样。
这是他长这么大,第一次离开垚县,第一次乘坐如此豪华的马车,更是第一次与县令、师爷这样平日里只敢远远仰望的大人物同行。
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熟悉景致,少年心中既充满了对未知旅途和繁华京城的无限憧憬,又因为这骤然改变的环境和身边的大人物而显得颇为拘谨和紧张。
他端端正正地坐在车厢角落,双手放在膝盖上,腰板挺得笔直,连大气都不敢多喘一口,只是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,却带着少年人特有的好奇,不断地透过车窗打量着外面的一切。
苏玉娘看出了儿子的紧张,却并未点破。
有些见识,需要亲身经历;有些成长,也需要在历练中完成。她只是引导着他多看、多听、多想。
“家仁,你看这路边的田地,”马车驶出垚县地界,进入官道,苏玉娘指着窗外那些景象,语气平和地说道。
越往外走,旱情的影响就越发明显,田地大片龟裂,枯黄的作物稀稀拉拉地倒伏在地里,路边偶尔能看到面黄肌瘦、眼神麻木的流民蜷缩在树荫下。
“这就是咱们要用土豆和红薯去改变的景象。记住这番情景,想想咱们苏家村如今的光景,想想后山那片试验田里的收成。”
她目光温和却带着力量地看着儿子:“你此行,不仅仅是跟着娘和阿爷去京城见世面,更是身负着责任。”
“你要把咱们垚县如何克服旱情、找到活路的法子带到京城去,找到让百姓吃饱饭的路!”
苏老汉也在一旁,用他那布满老茧的手拍了拍孙子的肩膀,语气带着几分郑重和期许:“是啊,家仁,你如今也是读书人了,脑子比阿爷灵光。”
“你得把咱们怎么选种、怎么育苗、怎么施肥、怎么储存的法子都牢牢记在心里!一路上多看多问多琢磨!到时候到了京城,那些官老爷们若是问起来,你也能替阿爷分担分担,把话说清楚,说周全!”
苏家仁听着母亲和阿爷的话,看着窗外那令人心悸的景象,再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,原本的紧张和拘谨渐渐被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所取代。
他用力地点了点头,眼神变得格外认真:“娘,阿爷,我记住了!”
或许是看出了苏家仁的潜力,或许是真心爱才,周县令在路途歇息时,也时常会有意无意地考校苏家仁。
有时是随口问一句《论语》里的典故,看他如何应对;有时是指着沿途的某处景象,问他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或农事有何看法;有时甚至会聊起一些当前的政令或时事,听听他的见解。
苏家仁虽然年纪尚小,历练不足,但在张夫子教导下,四书五经的根基打得颇为扎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