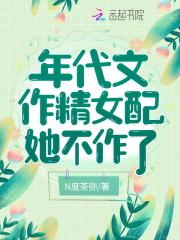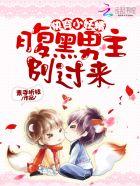精英小说>这个导演没有格局 > 第383章 乡村大舞台有胆你就来(第1页)
第383章 乡村大舞台有胆你就来(第1页)
孟梓义的反应很快,听到摇一摇组合,她就说道:“遥遥的名字加上我名字里的义字,摇一摇确实可以!”
随后又反应过来:“不对!陈遥只有一个摇,摇一摇是两个摇。
表哥,你不会想把姜沛瑶也摇进来吧?。。。
江一锋放下手机,窗外的天光正一寸寸爬上办公桌沿。他没开灯,任晨色在纸堆上缓缓流动。桌角那杯凉透的茶泛着微黄,像一段被搁置却未冷却的记忆。他盯着短信看了许久,手指轻轻敲击桌面,节奏缓慢而坚定,仿佛在为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打拍子。
七点整,刘椿准时推门进来,手里抱着一台加密硬盘,脸色凝重。“已经传完了,所有原始素材、剧本草稿、录音记录,全部进了瑞士服务器。国内只留一份物理隔离的备份,藏在公司地下档案室。”
“好。”江一锋点头,“通知王小柱,闭门会定在今天下午三点,地点换到郊区老厂房,不要用车牌登记,所有人步行进入。”
“你真打算硬扛?”刘椿皱眉,“对方可是《审核通则》起草组的人,这已经不是普通举报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江一锋站起身,走到窗前,“但他们犯了个错??他们以为‘美化’是个贬义词。可如果一个人疯了还能被理解,一个破碎的灵魂还能被看见,那这种‘美化’,正是我们最该做的。”
刘椿沉默片刻,忽然笑了:“你还真是越来越不像个商人了。”
“我从没想当商人。”江一锋回头看他,“我只是不想让真实的声音,死在剪辑台前。”
下午两点五十分,废弃纺织厂的铁门悄然开启。这里曾是九十年代国营棉纺厂的仓库,如今空旷如荒原,只有几盏应急灯投下昏黄光影。王小柱最先到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,手里拎着保温杯,神情疲惫却眼神锐利。随后陆续来了六位编剧,都是江一锋亲自挑选的老班底,有写过精神病院纪实剧的周砚,有专攻社会边缘题材的林晚,还有擅长心理悬疑结构的赵沉舟。没人说话,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近乎肃穆的紧张。
三点整,江一锋走进来,身后跟着李虹。她抱着一叠文件,面色平静,但眼底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。
“人都到齐了。”江一锋站在中央,声音不高,却穿透整个空间,“有人想让我们停下《心魇》。理由是??涉嫌美化精神疾病。”
众人面面相觑。
王小柱冷笑一声:“所以现在连共情都算违法了?”
“不是违法。”李虹翻开文件,“是恐惧。他们怕观众看完会质疑‘正常’的定义,怕人们开始问:到底是谁判定谁不正常?是我们病了,还是这个世界病了?”
江一锋接过话:“《镜中人》讲的是双重人格,但它真正写的,是一个男人如何面对自己不敢承认的创伤。他不是疯,他是痛得太久,只能分裂自己来活下去。如果我们因此说他在‘美化分裂’,那等于否定了所有幸存者的挣扎。”
周砚低声接道:“就像汶川地震后,有多少救援队员得了PTSD却被当成懦夫?他们不是软弱,是背负了太多不该由一个人承担的重量。”
“对。”江一锋点头,“所以我们不改。不仅不改,还要把第二集《父亲的枪》拍得更狠。”
赵沉舟皱眉:“这一集原型是那个退役警察吧?儿子误杀平民被判死刑,他自己查案发现真凶另有其人,但证据被上级压下……最后他在幻觉中不断回到案发现场,举枪对准自己的头?”
“没错。”江一锋目光沉静,“但他最终没有扣下扳机。他在梦境里和死去的儿子对话,儿子说:‘爸,放下枪,你还活着,就得替我说话。’那一刻,他哭着把枪扔进河里。这不是鼓吹暴力,这是教人如何带着创伤继续走。”
林晚轻声问:“可审查那边……”
“他们会看到一个‘科幻设定’。”李虹插话,“我们会加入脑波监测仪、虚拟现实回溯系统这些元素,把心理治疗包装成未来科技实验。人物的病症,叫‘记忆重构障碍’,治疗过程叫‘意识校准’。术语一换,外壳一包,他们就难下手。”
王小柱咧嘴一笑:“又是你那一套‘戴着镣铐跳舞’?”
“不。”江一锋纠正,“这次我们要让他们看清楚舞姿,再决定要不要砍掉舞者的脚。”
会议持续到深夜。七个人围坐一圈,逐帧讨论每一句台词、每一个镜头的情绪走向。他们重新梳理了《心魇》的整体脉络:六集短剧,每集聚焦一种心理困境,但暗线串联起同一个主题??**语言无法抵达的地方,灵魂仍在呼救**。
第五集《夜行者》,讲述一位夜班出租车司机长期遭受幻听,总听见乘客说“下一个路口左转”,而那条路通向一座早已拆除的精神病院;
第六集《她说》,改编自真实事件,一位女性在遭遇性侵后患上解离性失忆,多年后通过绘画唤醒记忆,却因“缺乏物证”无法立案,最终她在展览现场对着镜头说出那句:“我说过,只是你们没信。”
“最后一集的名字,就叫《她说过》。”江一锋写下标题,笔尖用力,几乎划破纸张。